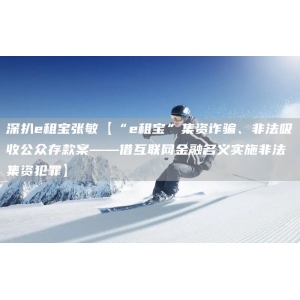一顆心值多少錢【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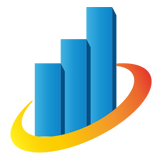 2023-01-07 07:34:36財都小生
2023-01-07 07:34:36財都小生“心”到底是什么?
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,我們常常看到“心”這個概念,比如陽明“心”學;比如相由心生;比如某某“心”不好等。
在這類的語境下,“心”指的不是心臟,而是和現代生理學上的“腦”有更多共通之處。

但心又不同于腦,腦強調的是理性的思考,而用許倬云先生的原話講,“心是感情和感官轉換的地方”。
人的感官在外界收到了信息,在心這個地方組織起來,激起感情的反應;組織起來的信息也被儲存起來,久而久之,形成了一個數據庫,這個數據庫里有人的“感覺、知識、理解,甚至包括智慧的總和。”許先生說:心“是主導人性格最內在的一個總機關。”
許先生在《往里走,安頓自己》這本書里舉了這樣一個例子:
1950年,許先生20歲,在臺灣大學讀二年級。在學校附近,有一個軍隊眷屬的安置地,臺灣的說法叫“眷村”。那時候,國民黨的殘兵敗將帶著家眷,被安置在這里。他們用竹子和水泥建起簡陋的房子,形成了聚落。這些老兵對大陸的家鄉是非常想念的。有一次,他們找來一個劇團,給眷村的居民表演京劇,唱的是《四郎探母》。熟悉京劇的朋友對這一出戲應該很熟。這是楊家將的故事,楊四郎本來是宋朝的武將,武藝高強,但在金沙灘一戰被敵對的遼國俘虜。楊四郎在遼國改了名字,生活了十四年,還娶了遼國的公主,當上了駙馬。可就在這時,他接到消息說,他的母親佘太君押送糧草,在邊塞碰上了遼軍。
兩軍對壘,一面是自己的祖國和母親,一面是自己新成立的家庭,楊四郎一時只有情感上的沖動,沒了理性上的主意。他先是突破關口,私自跑到宋朝的軍營里來,為的是和多年不見的母親見上一面。隨后,他又舍不下遼國的妻子和孩子,轉身跑回了遼國。這一來一去,楊四郎先是把遼國的家人置于危險之中,爾后又拋下了自己的老母親。戲劇沖突如同刀山,把他推上了矛盾的頂峰,讓他不得不一再背棄無法背棄的人。就在這樣的一個故事里,楊四郎見到了母親,他跪在地上,膝蓋著地爬到母親身邊,把頭放在母親的膝上,叫了一聲:“娘啊——”
許先生回憶說,他當時和眷村的居民們一起看那出戲,那一聲“娘啊——”穿透了每一個人的內心,痛苦、悲涼、無奈,在空氣里回旋,全場一千多名觀眾,男女老少,號啕大哭。